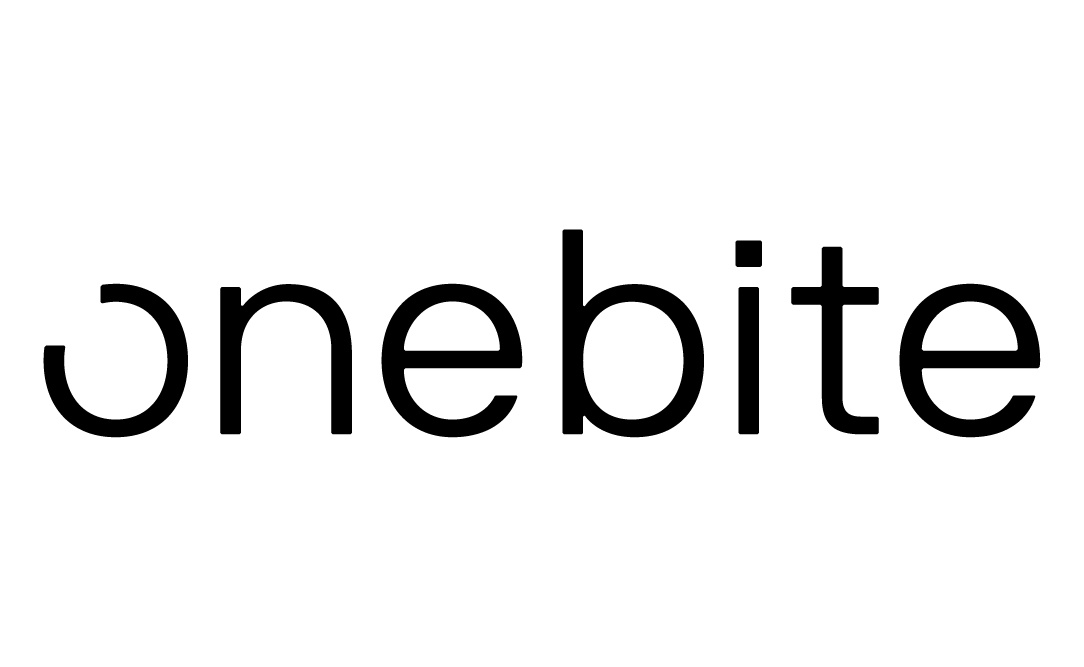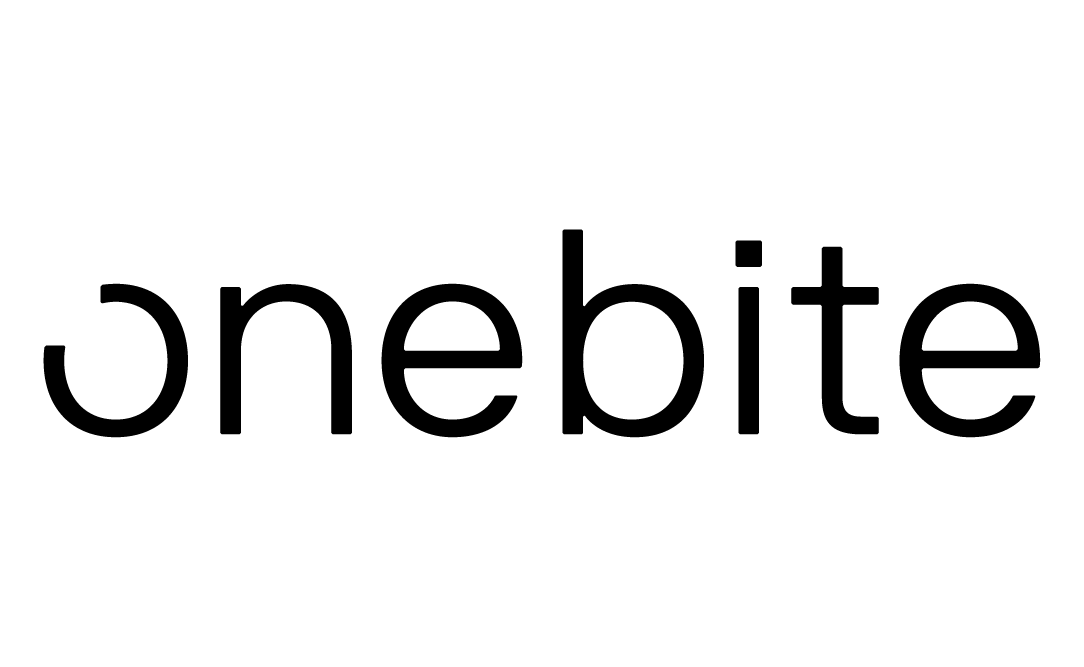「生前」好走:有好好說再見嗎?




在香港,平均每日死一百一十六人,不足十三分鐘便有一人去世,「死亡」是一個大部分人不願意提及,但又一定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面對的境況。試問自己:死亡突然到來的那一刻,是否會手足無措?只記得照傳統跟著做,把喪事辦好,或許因為很倉促甚至都沒時間表達悲傷,然而儀式結束後,情緒撲面而來。香港每年超過四萬人死亡,其中因而抑鬱的親友約有兩成[1]。從被告知重症,走完殯葬儀式,見證親友離世,臨終這最後一程對病人和家人都影響頗大,如若處理不好,留下的遺憾和內疚可能會許久都無法了結。死亡如此令人措手不及,若有選擇,回到生前,一定都想好好善終,減少逝者及親友的遺憾,走好人生最後一程。「死亡」是個複雜且沈重的議題,本團隊將基於香港的政策體系,民眾偏好及空間規劃,分兩個系列進行剖析:「生前」好走和「死後」走好。
全球視野:各國如何詮釋「Palliative Care」?
提到「生前」好走,最重要的莫過於全方位照顧患者的處境,儘量減輕其身心靈的痛苦,提供如意的生活質素。這裡不得不提到一個概念「Palliative Care」,世界衛生組織在二零零二年給出定義,病人確診致命或是不可逆轉之疾病,且一些積極治療已經不起作用甚至會導致更大傷害時,患者有權接受「Palliative Care」以保持生活質素。至於中文解釋,各地區有不同說法:台灣稱作「安寧療護」或「安寧照顧」;內地稱作「姑息治療」,也會偶爾使用「緩和治療」或是「寧養照顧」;香港則有更多不同的稱謂,九零年代的「善終服務」(Hospice Care)、「紓緩治療」到李嘉誠基金會資助時用的「寧養服務」和「寧養中心」,今年賽馬會贊助時用的是「安寧在家」、「安寧頌」或是「安好居家寧養服務」等等。但無論名稱為何,本質都旨在整體提高病患的死亡品質,那香港在這方面進展如何呢?
香港於一九九八年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紓緩治療專科資格的地區。然而,據二零一五年的《經濟學人》「死亡品質指數」(Quality of Death Index)研究報告顯示,香港在八十個國家中排名第二十二位,落後於許多亞洲主要發達國家,例如台灣,新加坡,日本和韓國,其中台灣今年大幅超越香港,領先亞洲第一,排名全球第六。全球都在積極應對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所造成的問題,各地區都愈來愈重視臨終患者的死亡品質,香港發生什麼事?
臨終關懷的挑戰:香港如何突破質素瓶頸?多方參與才能改變現狀!
香港在「二零一五全球死亡品質指數」研究報告中表現較差的有三,其一是「紓緩治療與醫療環境」,報告指出香港在「整體醫療支出、基於研究評估政策可用性,以及提供紓緩治療服務的能力」方面得分相對較低,僅得五十點四分,甚至低於中等收入國家巴拿馬和低收入國家蒙古國,得分最高的英國有八十五分,亞洲排名第一的台灣有八十分,而其中香港可以提供紓緩治療能力的估算值更低至百分之七[2]。換言之,香港去年離世的五萬七千人中,僅有能力向其中四千人提供紓緩治療服務。除了醫管局以外,還有食物及衛生局、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和一些民間團體都在提供不同類型的紓緩治療服務,但是並沒有政策令各部門合作,服務非常零碎[3]。因應「好走」倡議,兩千年醫管局轄下的醫院大約有三百張紓緩治療病床,截止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一八年底,也僅有十六家公立醫院共提供約三百六十張病床,據最新數據顯示,明愛醫院已有四十張病床,較十年前僅多出十張,而一些醫院撥出來的「療養病床」還要排期好一段時間,反觀台灣的人口是香港的兩倍,但已有五十二家醫院提供「安寧病房」,約有七百張紓緩治療病床,再次說明香港提供紓緩治療服務的能力相當有限。
其二是「公眾參與」,香港僅得三十二點五分,甚至不合格,並與大多數未發展國家同名。二零一五的研究報告指出在香港「很少可以從政府網站和社區機構中獲得有關紓緩治療的資訊,公眾對於紓緩治療服務的了解和認識有限,且社區很少提供有關紓緩治療的培訓」[2]。其後,香港政府大力推動醫管局發布《紓緩治療服務策略》,並於二零一九年通過「預設照顧計劃指引」,旨在告知病人有權預先決定臨終意願,推廣紓緩治療服務。然而,據二零二三年最新數據「香港安寧照顧服務社區調查」[4],及「香港臨終關懷定性研究」報告顯示[5],有近八成的市民沒聽說過預設醫療指示,大多數人仍然不認識紓緩治療服務,而近九成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患有絕症,寧願接受紓緩治療服務也不願意痛苦地延長生命。
其三是「人力資源」,香港得分六十二點一分排名第二十,勉強合格,但也遠低於排名第九的台灣。報告指出香港「較缺乏受過紓緩治療專業訓練的專家、醫療專業人士和護理人員,無法確保提供高品質的紓緩治療服務」[2],醫護界普遍對紓緩治療認識不深,甚至存有誤解。儘管公立醫院很有意願去成立紓緩治療團隊,但始終人手不夠,選擇專攻紓緩治療方向的醫護人員並不多。香港的十六家公立醫院都已有專門的紓緩病房,甚至有公立的白普理寧養中心是專門為晚期病人而設的療養院,且等候時間一般不超過兩週[3],這些地點提供的服務包括住院紓緩服務、門診紓緩治療、家居紓緩治療、紓緩醫學診症組,及日間舒緩治療等,服務內容多樣,並由跨專業的團隊提供,包括紓緩治療專家、護士、臨床心理學家、醫務社工、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營養師、其他專職醫療人員、靈性工作者和義工。截止二零一五年數據統計,一千位內科醫生裡,只有二十六人選擇紓緩治療科,全港在公營紓緩治療病房工作的護士一共也僅有兩百人[3],截止二零一九年也僅有約四十名醫生選擇紓緩治療科及共三百名護士,而同年台灣已有八百名專科醫師投入紓緩治療。而部分紓緩治療的專家及醫護人員對醫院提供的服務並不熟悉,導致並不能給患者提供正確的資訊。可見,並不是香港沒提供紓緩治療服務的選項,而是很少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和義工,民眾獲得正確且有效的資訊也非常有限。
十年後,香港醫療服務系統恐瀕臨「崩潰」,臨終患者又該如何「好走」?
全球各地區每年死亡人數持續上升,香港也不例外。據統計,二零一四年香港死亡人數接近四萬六千人,二零二四年香港死亡人數接近五萬七千人,政府預計十年後將增加至六萬九千人,二零四六年甚至將高達九萬兩千人[1]。香港目前的死亡人數中,有超過九成是在公立醫院去世,然而針對紓緩治療服務的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都遠不敷需,若繼續如此,香港的醫療服務系統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而對臨終病人的護理服務質量也遠遠無法達到預期。除此之外,亦有研究表明香港人也希望「回到社區,在熟悉的環境下接受護理,走完人生最後一程」,且有專家表示「我們必須加強非住院及外展服務,鼓勵紓緩治療人員與其他醫療專業人員緊密合作,並切實支援社區的非醫療照顧者,以達『持續護理』的整體目標,為末期或晚期病人提供更具自主性和令人明確心安的服務」[3]。
全球排名最高的英國每年約有五十萬人死亡,「少過六成死在醫院,兩成人在護理院,近兩成人在家裡離世,百分之四在養老院裡[3]」,截止二零一三年,仍有超過一半的死亡發生在醫院外,在家離世的比例更上升至近三成 [6]。而亞洲排名第一的台灣每年約有十六萬人死亡,市民仍然視在家離世是傳統文化,大多數人都比較支持,因而有近四成人是在家離世,甚至與死在醫院的人數相近。下一篇的吉人吉事將詳細解讀英國和台灣是怎麼做到緩解醫療系統壓力?在紓緩治療服務和人力資源上跟香港的差別是怎樣?而在城市空間規劃上,他們又是如何支持市民在社區以至於家中離世?如何在「生前」好走?
註:
[1] 數據來自政府開放數據平台「死亡統計」以及陳曉蕾《香港好走》系列圖書
[2] 根據據二零一五年的《經濟學人》(the Intelligence Unit of the Economist)「死亡品質指數」(Quality of Death Index):紓緩治療能力的估算值(Capacity of deliver palliative care services)= <接受病人並在家庭和醫療設施中提供服務> / <特定年份的死亡人數>
[3] 部分數據源於陳曉蕾《香港好走》系列圖書:《怎照顧》,《有選擇》,《死在香港見棺材》
[4]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近5.2億港元,於2016年策劃及開展推行為期十年的「賽馬會安寧頌」計劃,聯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及社會行政學系展開調查
[6] 數據來源於GOV.UK,Official Statistics,Palliative and end of life care profiles January 2025 update: statistical commentary
你可能對以下吉人吉事有興趣:
You may also be interested in these GUTS Stories: